原標題:百年一書
——樊錦詩和《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的編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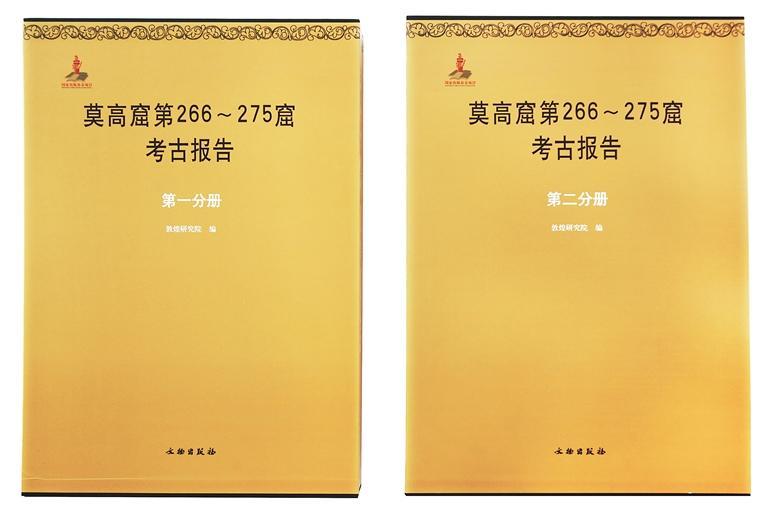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編寫組現場調查莫高窟第275窟。

敦煌莫高窟。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謝志娟

正在閱讀考古報告的樊錦詩。

2020年,樊錦詩在莫高窟第254窟指導《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第二卷編寫工作。

樊錦詩帶領項目團隊在莫高窟第275窟核對石窟考古報告測繪圖。

2007年,為石窟考古報告評議手工測繪圖。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謝志娟
1963年,考古學界泰斗蘇秉琦對即將前往敦煌工作的樊錦詩說:你去那里是要編寫考古報告的。考古報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樣,非常重要,必須得好好搞。
那一年,樊錦詩25歲。偌大一副重擔落在這個面龐還有點“嬰兒肥”的小女子身上。正青春的她哪知此后的路有多難。
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出版。
那一年,樊錦詩73歲。48年里,師長的話一直在耳邊回響,無論境遇如何變,無論過程有多難,她從沒想過放棄。至此時,終于交上第一份答卷。
2024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報告》出版。
這一年,樊錦詩86歲。發已白、腰已彎,編撰工作卻未停下。與此同時,第三、四卷,第五、六卷的編撰同步推進。參與其中的26歲的楊麒玉說:“要完成百卷目標,即使步履不停,大概到我孫女那一代也出不完。”
從學界泰斗到“敦煌女兒”,再到剛剛參加工作的新人,百卷考古報告為何成為學人百年心愿?
因為有它,敦煌石窟可“重生”。
“做不出來考古報告,我沒法向兩位老先生交待。”
時間是條河,綿延前行。
穿越1600年的重重歲月,今天的我們仍能看到莫高窟735個洞窟、4.5萬平方米壁畫、2000多身彩塑的精美絕倫,是時間對于我們的厚愛。
但時間同樣無情。與世界上現存或已遭破壞消失的其他石窟一樣,科學的保護縱能延長莫高窟的壽命,卻很難阻止其逐漸發生劣化,無法使其永存。
“山體巖石有很多縫隙,敦煌雨水雖少,但也會有,水進去了出不來。水的滲入,造成巖體中的鈉、鉀等可溶性鹽類運移,危及黏結在巖體上用泥土制的壁畫,造成壁畫起甲、酥堿等種種病害……”每每說起莫高窟,樊錦詩的焦慮之情溢于言表。“如果再有大地震,我們有再大的本事也擋不住。雖然我們在搞壁畫數字化,但它不會‘說話’,所以一定要搞考古報告。我的業師宿白先生要求到什么地步呢?如果洞窟有一天毀了,根據考古報告是能復原重建起來的。”
樊錦詩口中的考古報告絕非只編一兩卷而已,而是“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三處石窟寺的數百個洞窟均應編撰,以達到永遠留存敦煌石窟完整、科學、系統的檔案資料的目的”。
與敦煌莫高窟有著相同地理位置、歷史背景、題材內容、藝術特征的敦煌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共屬敦煌佛教石窟藝術范疇,統稱為敦煌石窟。1957年,在時任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主持下,曾制訂過編輯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計劃,雖只是一個“記錄性圖錄”的計劃,但在當時已難能可貴。
1962年9月,樊錦詩在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宿白先生帶領下前往莫高窟實習。在此期間,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做了著名的《敦煌七講》學術講座,首次發表了他經過長期思考探索而創立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理論和方法。
1963年,樊錦詩從北京大學畢業。離校前,蘇秉琦先生專門找她談話,他慈祥地對她說:“你去的是敦煌,將來你要編寫考古報告,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漢代歷史,人家會問,你看過《史記》沒有?看過《漢書》沒有?不會問你看沒看過某某的文章。考古報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樣,非常重要,必須得好好搞。”
25歲的樊錦詩人還沒到敦煌,先領了個需用一生作答的考題。
“我到了敦煌,開始三年,學生娃娃的水平,能搞成個什么名堂?也就是把實習的方法用上去。”之后,又經歷一些波折。1977年,樊錦詩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從此承擔起日益繁重的管理職責:“開始也沒認為管理是門學問,后來發現,管理不但是門學問,還是門大學問。而我越投入精力搞管理,就越沒時間搞研究。”
交作業、還債、考古報告……成為樊錦詩口中常說的詞,不知緣由的人哪知她的心結,“做不出來考古報告,我沒法向兩位老先生交待。”在內心,她也一次次問自己,“如果不把考古報告做出來,我這輩子到敦煌干什么來了?”
“總得有人下‘笨功夫’。”
時間是座山,壘石成峰。
《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的編撰為何如此艱難?
首先體量巨大。在樊錦詩的構想里,將敦煌莫高窟等三處石窟寺的數百個洞窟全部收錄的考古報告,應逐窟記錄洞窟位置、窟外立面、洞窟結構、洞窟塑像和壁畫以及保存狀況,并附屬題記、碑刻銘記等全部內容。此外,還要記錄附近的舍利塔群和遺跡,流散在國外的彩塑、壁畫等,同時要盡可能收錄、匯集前人調查、記錄的成果,以及有關洞窟的研究文獻目錄,還包括彩塑和壁畫制作材料的科學分析實驗報告……何等浩繁!
其次,《敦煌石窟全集》分卷計劃怎么做才合理?“那么多洞窟,總不能大窟是一卷,小窟也是一卷,這樣顯然不合理。”
如何分卷,眾說紛紜:有的說以已形成的現狀排列為順序,有的說以洞窟編號為順序,有的說重點洞窟排在前、非重點洞窟排在后,又有的說對哪個洞窟有興趣就先做哪個……樊錦詩說,重點窟和非重點窟是人為的,不是客觀的;百十年來國內外已有不少洞窟編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編號法,這也都是人為的;以已形成的石窟現狀排列是混亂的;想搞哪個洞窟就搞哪個洞窟,就更亂了。
站在洞窟前,樊錦詩無數次地琢磨,她的心里漸漸有了較為清晰的脈絡:“為了避免編排不當造成撰寫時的混亂和重復,避免各分卷分量的畸輕畸重,或洞窟組合過多過少,避免只重視重點洞窟,而忽略其他洞窟的問題發生,所有分卷編排順序以洞窟建造時代前后順序為脈絡,又考慮洞窟排列布局走向與形成的現狀,每個分卷的洞窟組合,均以典型洞窟為主,與鄰近的同時代或不同時代的若干非典型洞窟形成各分卷的組合,進行全面規劃和編排分卷。”
考古報告此前多年難以出爐還與技術條件不成熟有關。“最早的時候,我們誰見過電腦呀,繪圖用的是‘小平板’,測量用的是垂球、三角板。測量的人爬上爬下,繪圖的人說往左往右……又慢又不準。洞窟不像我們住的房子那么四四方方,洞窟里不是壁畫就是塑像,又不能搬動,測量先就是個大難題。”直到近些年,三維激光掃描測量儀器問世、高精度數據采集、數字攝影、用電腦軟件精確繪圖等技術成熟,才使全面、高效、非接觸地獲取洞窟三維數據、高清圖像并進行虛擬拼合與重建成為可能。
知其艱難者,質疑“你們做得出來嗎?”
的確,考古報告的文字、攝影、測繪記錄和編撰絕非簡單記載,還需深入調查、探索、考證與研究。對洞窟的斷代、內容考釋、藝術風格辨析等均需嚴謹學術支撐,耗時漫長。
不知其艱難者,也質疑:“怎么那么慢?”
“真正的事情是花功夫做出來的。”樊錦詩說,短平快的事情,立不住,總得有人下“笨功夫”。
還難在專業人才的缺乏,“開始就我一個人,后來有了團隊,可是老的老、小的小。”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努力,考古、測繪、數字化攝影、化學、物理等學科的專業人員紛紛參與其中,分工合作。而樊錦詩的心里,有總譜。
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出版,這項世紀工程終獲重大突破,為后續工作提供了重要范本。
“一次次失敗,連滾帶爬,終于出來了。”樊錦詩說她肯定看不到100卷完成的時刻,但“我把頭開了”。
“我們要為創造它的祖先負責,為國家負責,為讀者負責。”
時間是把尺,可量歲月。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報告的出版,引起學界的反響。國學大師饒宗頤評價它“既真且確,精致絕倫,敦煌學又進一境”。英國倫敦大學名譽教授韋陀說:“從未有過的資料系統完整的科學性,將為中國其他石窟寺遺址的考古報告提供標準與模式。”
第一卷獲得第七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獎”“法蘭西學院汪德邁中國學獎”等重要獎項。
第二卷于2025年6月獲評2024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
面對認可,樊錦詩告誡團隊成員:“不能驕傲,我們仍然在摸索和改進中。”
也有人會說,這是什么學問嗎?不就是記錄資料嗎?事實上,這種要下“笨功夫”的基礎研究非常艱難,很容易出錯,即使是尋找一個合適用詞,已讓人“搜腸刮肚,才盡詞窮”。樊錦詩說:“不能亂用形容詞,比如說‘漂亮’,什么叫漂亮,它不是一個準確的描述,所以說考古報告的文字比較枯燥。這是要留史的,不能對付。我們要為創造它的祖先負責,為國家負責,為讀者負責。”
第一卷出版時,蘇秉琦先生已作古多年,宿白先生也已89歲。數十年里,宿白先生每見樊錦詩總要問到考古報告,樊錦詩回憶道:“宿白先生曾‘嚇唬’我,說要派人去看我怎么做的。我說宿先生您親自來看不是更好嘛。我們做出來,讓宿先生‘找毛病’,最后,是宿先生親自說可以出版了。他又說:‘樊錦詩,你搞這一卷就完了嗎?’我說第二卷已經開始了。”
2024年1月,《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報告》出版,而于2018年離世的宿白先生已經看不到了。
此時的樊錦詩已經86歲了,她說:“做完第二卷我就‘金盆洗手’啦。”可她又說:“這個報告是我弄起來的,還得往前走。我跟你說,做事就是要堅持,要不然你永遠做不成事。踏踏實實把一件件小事做好,每個人把本職工作做好,這個國家就好了。這個要求好像很低,其實很高。”
“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要重視這些學科,確保有人做、有傳承。”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令樊錦詩記憶猶新。2019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時強調:“把莫高窟保護好,把敦煌文化傳承好,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進步應負的責任。希望大家再接再厲,努力把研究院建設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
諄諄囑托,銘記在心。
樊錦詩常跟年輕人說,國家把你培養出來,你怎么報國?就是要踏踏實實做好本職工作。多年后,洞窟不是今天的模樣或者不存在了,可還有考古報告在,就像《史記》還在。它為人類留存了一份記憶,給未來留下一把鑰匙。
記者手記
“真正的事情是花功夫做出來的”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謝志娟
2024年初,再次前去莫高窟采訪時,在食堂遇到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看到我,她說:“第二卷出來了,你還沒看到吧?”馬上請身旁的年輕人去抱書。說是抱,是因為沉甸甸三大本,要用些力氣。
飯,暫且也不吃了。她推開面前極少極簡的一點飯菜,用紙巾仔細擦凈桌面,才打開比磚頭還厚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報告》,一頁頁慢慢翻著給我講……1057頁,若一天能完成一頁的工作量,也約需三年。
“敦煌女兒”樊錦詩對于我而言,是最為特殊的一位采訪對象。自22年前初次采訪后相識,之后無數次交談,幾乎每次都會聽她提起“考古報告”。
最初,我完全不明白這四個字的分量,不明白它對于樊錦詩而言,意味著什么。對于敦煌石窟而言,又意味著什么。
不就是一本工具書嗎?足夠細心足夠時間,應該就可以完成吧。
可是,一次次聽到她說:
——這個報告,很不好做啊。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也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問題。大環節里有許多小環節,小環節里有許多細節。
——我們現在已形成考古報告的工作團隊,可是老的老、小的小,我得想辦法往前推。
…………
經過她20多年的“專業輔導”,“考古報告”四個字終于印在了我的腦海里。那么厚重的專業書籍,作為一名非專業人員,我能讀懂的內容非常有限。可是,作為一名記者,我讀懂了樊錦詩60余年的牽腸掛肚。
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不能辜負的師長囑托、敦煌石窟的保護和研究所需……是責任,也是使命。這責任的分量,在她與莫高窟的朝夕相處中越來越凸顯,她將之扛在肩上60余年不敢放下。起起落落、反反復復,難以完成又必須完成的“考古報告”,既成她的“心病”,又是她的“心勁”。在編撰過程中,她對每個環節每個細節幾近苛刻的嚴格要求,是對這份沉甸甸的責任最負責任的落實。
放不下呀,這樣的敦煌、這樣的寶窟,終有一天會消失,沒有了就是沒有了。因為懂得這份珍貴價值和重要責任,所以執著要為敦煌石窟留下一份“傳記”與“畫像”。從圓臉愛笑的小姑娘到步履蹣跚的老者,編撰考古報告,不僅僅是她用60余年交給師長的一份作業,更是交給未來的一把鑰匙。
為此,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值得。
- 2025-12-16百年一書——樊錦詩和《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的編撰
- 2025-12-15甘肅文旅集團榮膺“2025中國旅游業先鋒力量”企業稱號
- 2025-12-15黃河蘭州段興起“天鵝經濟”
- 2025-12-15甘肅1600多年歷史的馬蹄寺石窟群“轉危為安”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











